冯翔|十八年的轮回
请你提供具体的“冯翔|十八年的轮回”相关内容呀,比如是他经历的具体事件、情感故事等,没有这些详细信息,我很难准确地写出 200 字的描述呢。

沈阳的医院水平在全国都是排得上号的。这家又是沈阳最好的大医院之一,尤其是心脏病治得好。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看病。
她也是,从吉林农村带着生命垂危的女儿来做手术,还好命保住了。今天出院。
踩着满地硬邦邦的冰雪走到院子里,我帮她拉开车门,她突然顿了一下,抱住我的胳膊嚎啕大哭,眼泪顺着苍老的皱纹流了一脸。旁边,两位从北京赶过来的记者在拍照。
那一刻,我一边掏出纸巾给她擦眼泪,一边望着天上飞过来飞过去的云,感受着耳边嗖嗖刮过的东北风,想起一些更久远的往事。
整整十八年前,也是在这个院子里,我们同一伙人干过同一件一模一样的事,把一些名词搅合在一起:
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,一个治不起病的女孩,一群身家百亿的富豪,一场搅动整个国家的争论……
而我,是唯一一个穿梭十八年的见证人。
这大概是我的人生至今最奇特的一次缘分。
现在这事情也过了一年了,我觉得也许可以说一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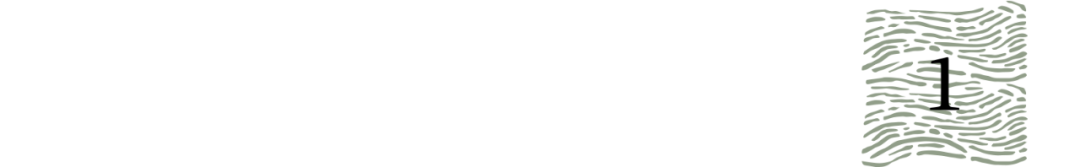
当我比现在年轻十多岁的时候,确切地说是2006年初,我在沈阳的一家都市报当记者。
那时候,媒体承担着很大一块社会需求,就像一个综合类的NGO。
穷人得了大病治不起、贫困生考上大学没学费的新闻,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,目的一般不明说:号召社会捐款。
就在那个一月,我先后写了三篇求助类报道,说白了就是募捐。其中一篇,是一个农民工因为被欠薪没钱去医院,他妻子寒冬腊月把孩子生在了大马路上。稿子发出去,读者果然捐了医药费,把生命垂危的孩子救活了。
写得多了,我总结出几条规律:越是本地的,越是“人祸”,当事人长得越好看,越表达将来要回报社会,越容易得到捐助。反之,就很难了。
那天,又一个求助的人来了。我扫了一眼,立即判断出这是一个没什么希望的求助对象。
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瘦长脸,穿着一身土里土气的西服,有些畏缩地站在我们报社的接待室里。他叫刘福成,是吉林四平一个贫困县的农民,后来我叫他“老刘”。
根据他带来的医院诊断书以及单据,事情是这样的:
他有个十七岁的大儿子,去年又添了一个小女儿刘帅。可这孩子几个月就被发现明显不对路,吃完奶也哭,脸通红,喘气呼哧呼哧的,明显是难受。经过镇上、市里和省会三级医院的诊断,刘帅很快就被确认为先天性心脏病。
她的病叫“永存动脉干”。简单地讲,就是由于先天发育畸形,心脏大动脉和通往肺部的动脉没有分开,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治疗,她很可能一岁之前就死于肺部感染和心力衰竭。每十万个新生儿之中只有三个这样倒霉的。
于是,老刘两口子心急火燎地带着女儿来沈阳看病。他们随身揣着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,上面记着五十三户亲戚、朋友、邻居的名字和借款数字,总额六万二千九百元。这六万多元,刚够刘帅前期的检查费用以及手术费。
当时东北还在下岗高峰期过后的阵痛阶段,穷得很。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,还是有很多人一个月只赚几百块钱。老刘一家更是平均每个月只有三百元出头,主要来自于他在农闲时干瓦匠活、在附近镇上打短工的报酬。
做完手术,女儿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,躺在ICU里每天的检查治疗费就是一千元左右。欠费催款单一张接着一张来了,老刘两口子唯一的办法,就是蹲在病房外头哭。
来我们报社之前,他已经找过一家本地最有名的电视新闻频道,被拒绝——“我们这里像你这样的太多了”。
说实话我非常理解,简直太理解了。我也想拒绝他。
忽然,他跟我说了一句话:
“我给中国的‘首富’写了求助信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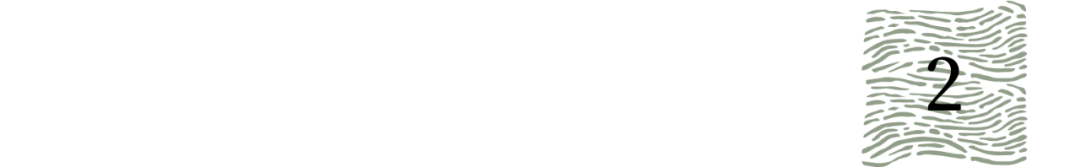
那一年,中国虽然总体还很穷,但GDP总额已经是世界排名第四,仅次于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。
社会上也已经有了几份富豪排行榜,有胡润的,也有福布斯的。当时前几名还是制造业的天下,互联网巨头们大多还没成气候。马化腾在福布斯排行榜上排名第35,马云排在第76,张一鸣大学刚毕业。
当年排名第一的中国首富,是一匹横空出世的黑马——四十三岁的施正荣,中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公司总经理,身家186亿。老刘正是在医院里看到我们报纸上一篇关于这位“首富”的报道,才下决心向他求助。
他给我口述了这封信的大意:
“施总经理,我此刻与你联系,就是希望你能伸出援助之手,奉献一颗爱心,救救我的孩子……”
“求您了,我给您跪下了!我一个农村人,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,上哪去弄这么多钱,求您了!……”
“普通老百姓也不富裕,我不想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负担。报纸上说,他(施正荣)是中国富豪,还说他打算拿出一部分钱成立慈善基金……”
而且,老刘求助的对象不止施正荣一个,还有几个当时如雷贯耳的名字:国美的黄光裕、盛大的陈天桥、联手创业的刘永行刘永好兄弟、网易的丁磊、万象集团的鲁冠球!都是这几年被评过“中国首富”的人,个个财产都在上百亿!
一个农民,竟然能想到给中国排名前几的首富求助,还能找到他们公司的名字,用特快专递寄过去?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。
经过进一步的接触、了解,我才明白:老刘虽然穷,四十多岁了没喝过可口可乐,但绝非一个普通的农民。
他从小被亲朋好友形容为“脑子够用”,考试成绩经常是第一第二,只是因为家里实在太穷才初二辍学。他跟在师傅身边看了几天,就学了一手瓦匠手艺;他甚至一边打零工,一边给长春电影制片厂投过自己创作的电影剧本。
这一次,他天天去网吧上网,靠自己摸索知道了这些富豪的名字,查到了他们的公司名字。
一个农民为了救自己重病的女儿向富豪求助,这是新闻吗?报社内部首先就有一场激烈的争论。最后我们社会新闻部的一位副主任的意见占了上风:“只要他写了信,本身就是新闻。”
当时是都市报野蛮生长的年代,报纸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,我们报纸尤甚。每天食堂门口都贴着告示:今天某篇车祸写得好,奖励一百元;某篇火灾比另一家报纸的少了一个新闻点,罚款五十元……我想,这可能也是报道得以发表的另一个原因。
几天后,我和一个同事共同署名的报道发了,题目叫《救女 穷父求助“中国富豪”》。
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风暴。
有人评价:“沈阳这家报纸何其无耻!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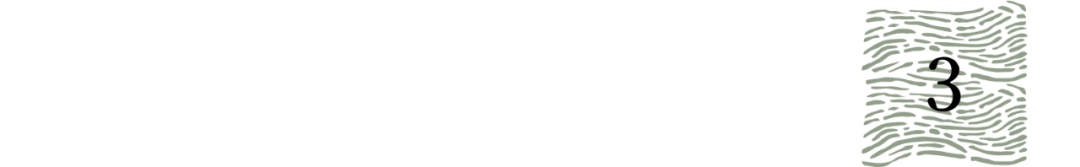
光央视就来了三个节目组,《社会记录》《今日说法》《正在关注》。
从最北边的黑龙江到最南边的海南,全中国几乎每个地区的报纸都报道了“穷父求助富豪救女事件”。这些报道,很多今天在网上还能查到。
吉林的媒体还直接跟我们联动,去了老刘的家。村长说:刘福成夫妇老实忠厚,他们的情况绝对属实。
新浪、搜狐、网易、人民网……都围绕这一事件做了专题,全国网民被搅动起来,在无数个论坛、聊天室甚至百度贴吧里不停地争论。
有人说:你们对这些富豪实施了舆论绑架;有人说:你们把他们架到了“道德烤箱”上。有人说得更直白:“沈阳这家报纸何其无耻!”
我很尊重的一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写了一篇文章,《“舆论绑架”与媒体逼视——论公共媒体对私人领域的僭越》,把这件事列进当年的“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十大热点事件”之一。里面有这样的话:“粗鲁而具有冒犯性的媒体让人人自危”,“这无异于挖掉了社会慈善的道德根基”。
他还把这篇文章收入自己的专著《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》,我后来翻过这本书。
我们也没有时间管这些争论,而是每天都在刊发追踪报道。
我天天追着那几家大公司,打电话问他们:你们收到信没有?是否准备捐款?同时还在报道里刊出那几封信的进度:今天,寄给某某公司的信件经邮政查询已经收到,收信人是……
然后,我再一趟一趟地从北向南穿过城市,顶着风雪去医院和小旅社里找刘福成:老刘,今天咱们写点儿啥?
老刘也真是聪明。每次都能拿出点灵感来:写一封感谢信、写一首诗,帮我们制造新闻。每次我委婉地跟他暗示,需要一些“将来我们一定回报社会”之类的言辞,他都能马上领会到,说得比我想要的还好。
这些操作,我们当然也清楚是有点不登大雅之堂的。那位新闻学教授批评得很对。
可是,不这么做,问题怎么解决呢?谁来救孩子的命?
那些年,坊间还流传着一句话:畸形的社会需要畸形的媒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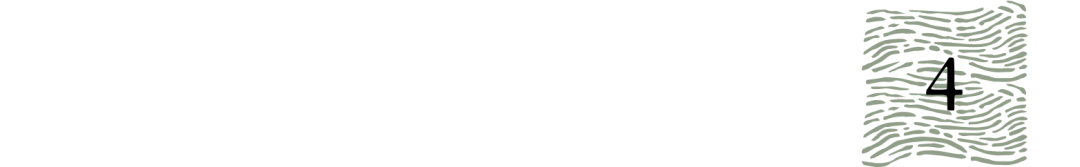
几大富豪里,我其实认为陈天桥最有可能捐款——这个人年轻、高调,像是会给社会捐款的样子。在电话里,我跟他的新闻发言人聊得也不错。上网查了一下,他居然是从复旦大学宣传部副部长任上被挖过去的。
最后,还是施正荣的女助理在电话里给了我一个肯定的回答:“我们捐助两万”。
那一刻就像被两万伏高压劈中,然而是幸福的。这位大姐的名字,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出手的还有另外两位富豪:黄光裕派国美的吉林分公司给刘福成一个五千块的红包;刘永行也捐了五千块。
虽然陈天桥没捐让我略失望,但这已经够了。跟几万块钱比,首富们的名字更重要。
医院把刘帅剩下的药费全免了,上了最好的措施最好的药,专门针对她组织专家会诊,还请出了一位老爷子。
这位老爷子已经八十四岁,戴着一副眼镜,瘦瘦的。他很认真,对央视记者谈了刘帅的病情,还送给老刘一盒茶叶。
他叫汪曾炜,是医院心血管外科的创始人。这个名字你是不是觉得眼熟?
对,他的堂哥叫汪曾祺——就你听说过的那个,写高邮咸鸭蛋很出名的作家。
汪曾祺还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他:“我有个堂弟,曾在县立中学踢毽子比赛中得过冠军。常因国文不及格,被一个姓高的老师打手心。后来忽然发愤用功,现在是全国有名的心脏外科专家,比我小一岁……”
老刘两口子自然也成了新闻人物。
小旅社免掉了他们每天五块钱的住宿费,还给换了一间阳光很好的大房间;附近一家大学的餐厅经理让他们免费吃饭,想吃啥吃啥。他们俩不敢夹肉菜,只敢夹豆芽。门口摆公用电话摊的大姐说:你们不容易,以前欠的电话费都不用给了。全国各地的捐款纷至沓来,连四平市政府都给拿了五千块。
终于,刘帅出院了。
老刘两口子连哭带笑,我的眼泪也差点出来。第一次看到她,挥动着小手,笑容那么可爱。虽然七十多天没见父母,她已经不认识他们了。
有个小伙,瘦几格拉的,头发挺长,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冲着我乐。
我问:你是谁?他说:我是刘福成大儿子,叫刘丰,特意来接我妹妹出院的。
我和他下次再见面就是十八年以后了。这是后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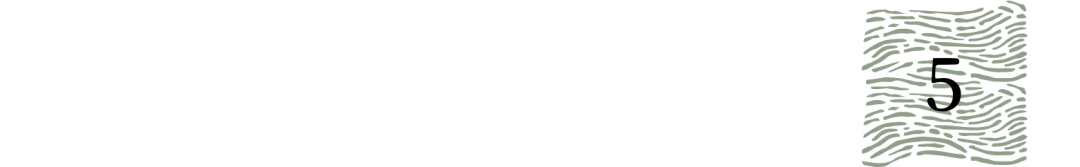
“刘帅现在不到三岁,顽皮可爱,言语清晰、反应灵敏,还能背出十几首唐诗,村里人都很喜欢她。只是身体还弱,经常感冒……”
后来,老刘给我写过一封信,说在沈阳那几个月是一场难忘的奇遇,说他会一直记得我们几个参与报道的记者。
凤凰卫视把他请去做了一场很大的节目,他专门为此穿上了结婚时做的一套西服。
两年后也就是2008年,他又来了沈阳一次,这时我才知道:原来,家乡人并没有袖手旁观。
沈阳一个很穷的县里有个小老板张总,悄悄给刘福成拿了两万块钱,叫他别跟别人说,这次他们两口子来探望这位恩人。“觉得要是再不说,那我刘福成太没有良心了。”
我跟着他们一起见了张总,得知当时他刚接手这家建筑公司,账户上只有三万块钱,他叫人拿了两万给刘福成。还让刘福成带几个老乡,去他那里当个小包工头。“你也看看马克思的资本论,学习学习怎么剥削剩余价值。”
但在那之后,我就没联系老刘了。离开沈阳去了北京,我也没告诉他新的电话号码。
原因有点可笑:担心自己总跟帮助过的采访对象联系,会让人家不舒服,觉得像欠了你什么似的。
之后,中国仿佛进入了一个加速度时代,发生了无数深刻改变社会面貌和个人感受的大事。仅2008年我亲身参加报道的就有汶川地震、北京奥运……
报纸很快就成了马车一样过气的东西,我任职的那家沈阳都市报最终关门,我们当年发在报社官网上的那些报道,都被雨打风吹去了。到北京这些年,我先后换了六七份工作,如今胡乱写写字,打打零工糊口。
我跟当初采访我的央视一位女编导成了朋友。有一次聊起这件事,我感叹那时候我才二十四岁,好年轻啊。她说:我怎么觉得你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挺油腻呢。我说:答对你们央视,太清纯了不行!
直到2021年末,我有一次去吉林出差的机会,才觉得应该跟老刘一家人联系一下:刘帅现在怎么样了?
我想起,当时给刘帅做手术的主刀医生跟我说的一句话:这孩子将来心脏一定还会出问题。
先上网搜,我发现刘福成这个名字除了当年的“穷父救女”,没有任何结果。打他当年的手机号码,变成了空号。
这不可能啊,老刘是一个如此聪明的农民,这么多年,他一定能折腾出一些事儿来!最起码也得干个合作社吧?
最后我终于联系到了那个村子一个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,相信他肯定认识老刘。
他果然认识,略带不耐烦地说了一句话:
“刘福成?这人早都死多少年了!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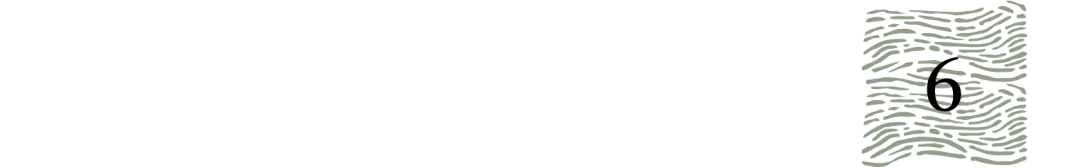
我站在刘家的院子里,看到一个黑胖黑胖的农村姑娘向我走来,脸上挂着怯生生的微笑。
那一瞬间,恍如隔世。这个胖丫,就是当年那个可爱的小婴儿吗?
老刘的妻子于金霞拉着我的手,一个劲地流眼泪。十几年没见,她苍老得厉害。
顶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,她把我带到一公里外一片白雪皑皑的黑土地,路上翻过一条沟的时候她还摔了一跤。那只是一座小土堆,连墓碑都没有。
“刘福成,冯老弟来看你来了。你说你咋不保佑你儿子呢?你走了这几年,咱们家人口咋就越来越少呢?……”
我一边听着她在寒风里呜咽,一边把从小卖店买的一瓶廉价白酒倒在土堆上,不响。
原来,当年张总没有食言,为了帮助老刘特意在四平成立了一家分公司。可老刘确实没有文化,搞不来,只能把一个发小介绍给张总,自己继续干小包工头。干了一年,他就把家里的债还清了,还贷款买了一辆手动挡的国产SUV,生活的前景似乎一下子变得很美好。
结果第二年,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突然心梗,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。其实说心梗也不确切,因为连尸检都没做。
不管是哪一种死法,他的死都给这个家庭致命的打击。
刘帅本来是个性格开朗的小姑娘,爱唱爱跳,多次扬言等哥哥结婚的时候她要做个现场致辞,“来两句”;每天晚上,老刘陪着她做功课,尤其是作文。一百二十分满分的语文卷纸,她往往能考一百多分。
父亲的死改变了她。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,母亲忙着打工顾不上她,学习再也没人能给她辅导。到初中的时候,她的成绩已经慢慢跟不上了,性格也变得沉默木讷。哥哥先后结了两次婚,婚礼上她都一声不吭。如今她下一步的选择,只是学美容美发还是直接出去打工。
大儿子刘丰离了婚,又做生意损失惨重;于金霞也试图改嫁过一次,结果没成功又回来了……如今,全家深陷贫困,债务缠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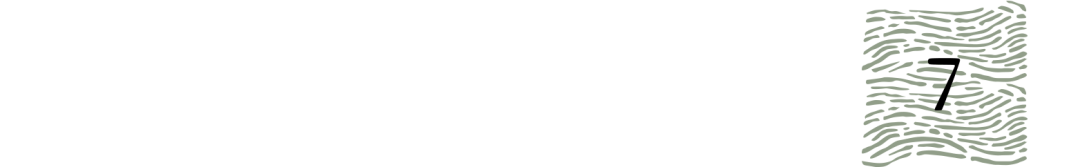
这么多年来,于金霞把当年的报纸和医院单据非常完好地保留着,却一次都没给女儿看过。在大无语之余,我觉得也不能苛责——毕竟,她是个文盲,连发微信都只能发语音,看不懂文字。
直到我这次来,刘帅才知道自己胸前的刀口居然有这样的来历。
“我以前觉得很自卑,现在觉得自己(的生命)来之不易,觉得我爸爸真的很厉害。我有这样一个爸爸,挺牛的。”
另外一些人物的命运却不一样了。
这次我顺路去沈阳看了张总。如今他的建筑生意干大了,全国有五十二家分公司,两三万员工。他个人当上了沈阳市摄影家协会的主席,还成了我母校辽宁大学的特聘教授!
“我就说老刘家的房子有问题。我们干建筑这么多年的,都知道。”他说:老刘突然去世的原因主要是风水。刘家的院门冲南,正对着大道,院门跟房屋正门、后门都在同一条直线上。这叫“穿心煞”,人也留不住,钱也留不住。“你现在看,院子大门已经挪开了。那是去年我去的时候发现不对,叫人给他扒了重盖的……”
老刘当年介绍给张总的那个发小还在,已经干到了集团的副总。这个沧海桑田的时代啊,有人从山顶掉进了海里,有人从海里登上了高山。
当年那几位首富,黄光裕入狱了,施正荣破产了,鲁冠球去世了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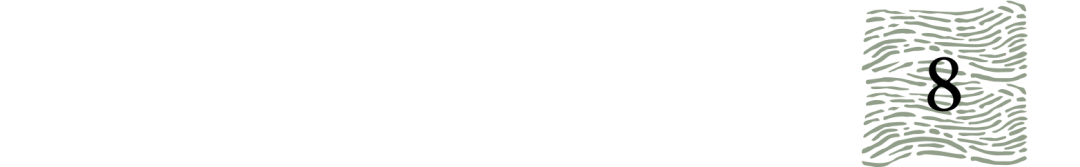
然后就是2024年1月21日,我正在北京逛书店,接到了于金霞的微信电话。
我一看她的头像就明白是怎么回事,瞬间充满了恐惧:刘帅的心脏肯定出事了。
十八年了,这一次,我们又该怎么办?难道再“绑架”一次富豪?
当年刘帅出院的时候,我就跟老刘一再说过:这种报道不能常态化,全中国的媒体只能这么干一次。第二次再“绑架”,不好使了。
而且确切地说,不是“我们”,只有“我”——老刘不在了,当年的同事们也星散四处。如今还能管这件事的,只有我一个人了。
所以我还是硬着头皮把电话接了。这次跟我联系的是刘丰,他正开着父亲当年留下的那辆手动挡SUV,连夜把妹妹往沈阳拉。还是那家医院。
还是找了个专给外地来就医的穷人住的那种小旅社。十八年过去,小旅社住宿费已经从每天五块钱涨到了四十块;但最后他们好说歹说,又给降到了二十块。
经过检查,为了保住刘帅的命,必须安装一个心脏起搏器。手术费和每天的检查治疗费,跟当年一样是他们高不可攀的数字。
我先给刘丰打了五千块钱,让他们在沈阳吃饭住宿;然后厚着脸皮又找了张总,他叫儿子加了刘丰微信,打来两万块钱,顿解一家人的燃眉之急。
接下来几天,我慢慢定定神,一步步琢磨出了该怎么办:刷脸找当地的媒体和外地的媒体朋友,先把“中国首富当年捐助的女孩如今生命垂危”这件事报道出去,再想办法筹钱。
新黄河、沈阳晚报、三联生活周刊、南方人物周刊、冰点、界面……朋友们陆续伸出了援手。跟十八年前一样,他们有的在沈阳报道,有的去了吉林刘家。我不再是记者,而是受访对象。虽然来采访我的记者都比我至少小一轮以上。
当年的两位老摄影同事给了我几张他们十八年前拍的照片:老刘夫妇蹲在医院病房门口写信的、哭泣的;刘帅手术后出院的,等等。我给媒体们发了过去。
同时我联系了轻松筹,让刘丰写了一些求助的文字。我先看了下,发现这哪里行呢,整个儿写成了一个普通农村女孩的求助,一个字都没提到当年的“穷父求助富豪救女”,那才是你们家最大的资产!
于是我重新写了一篇,用刘帅的口吻,题目就叫《我是一个普通女孩,中国最有钱的人救过我的命,可现在我又不得不向大家求助了》,发给了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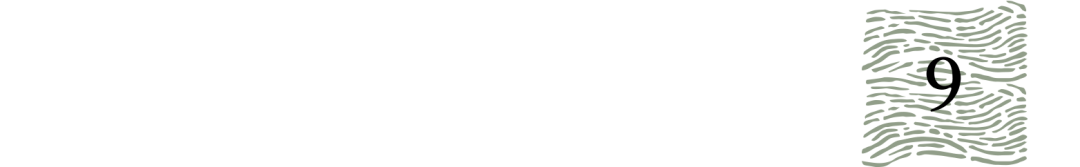
二月二十六日,我在朋友圈转发了这个轻松筹,同时自己捐了两千块钱进去。
这是一次切身感受世态炎凉的过程。之前我发了个朋友圈说要筹款,预热一下。关系最近的、最热心的朋友直接私信问你怎么了,次一些的在朋友圈底下留言问,也明显看得出有些人不想沾边。我都充分理解。
结果大概筹到了两万块钱。一位一直支持我的大哥捐了一千块,那位央视的女编导也捐了两百。还有两个朋友帮我把这条轻松筹转发了微博,阅读量不低。一个叫邹德怀,一个叫胖虎鲸。他们都是百万粉丝的大V,而且粉丝活性很高。
这些钱也就够几天的治疗费,手术费我们还得想办法。焦虑极了,我开始通过朋友联系各种基金会,不用说,最大的凭据还是当年“绑架富豪”的往事。
才过了两天,刘丰突然告诉我一个消息:
刘永好基金会的人找到了他,说:明天,新希望集团沈阳分公司的总经理会到医院去看你们:“一定会给你们家一定的资助!”
——首富刘永好还记得十八年前那个生命垂危的农村女孩,记得那五千块钱,然后又从网上看到她在求助,再次伸出援手!
在我看来,这比当年农民找到首富求助还要离奇,还要难以置信。
不禁想起余华的话:“我们老说文学高于现实,那是骗人的,根本不可能的!”
新希望集团拿了十万块,刘帅的手术费就这么解决了。
手术很成功,三天后就出院。我赶去了沈阳。
要分别了,于金霞突然抱着我的胳膊,在医院的院子里嚎啕大哭,哭了很久。这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。
十八年过去了,又是一个轮回。兜兜转转,循环往复。我们又回到了原点。
我其实也有点想哭,但可能这么多年记者当久了,已经麻木不仁,就只是给她擦了擦眼泪。
刘丰说:这是我妈在这几十天了,天天守着我妹妹操劳熬夜,太操心太压抑了。看到你,一下子爆发了。
后来她接受三联的记者采访时,解释了一下:“实在太累了。如果没有冯老弟,我们怎么活下来。”
其实我也觉得累极了,当天回到酒店一头就倒在床上。但还得先干一件事:
一个一个私信每个给轻松筹捐过钱的朋友,给他们汇报:手术成功了,你捐助的那个农村女孩已经出院。
有个姑娘说:
“第一次看到帮助过的人有回应,还是蛮惊喜蛮激动蛮感动的。”
“看到达者兼济天下,富人回馈社会,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希望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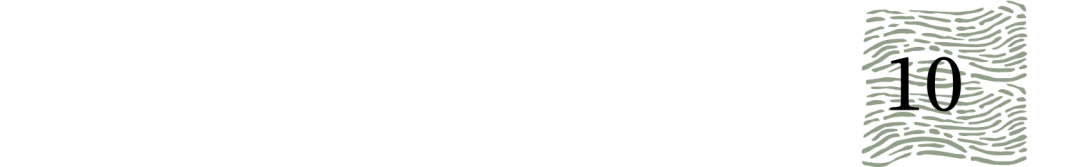
这件事又一年过去了,我跟刘家人基本没有联系过。
又回到了那种状态:“不要跟采访对象联系,省得像人家欠了你似的”。
这中间也有些朋友听说了,表扬我。我都实话实说:人家刘总和张总才是真英雄,我不过是个敲边鼓的。
其实我特别想去问问刘永行或者刘永好两位先生:你们是怎么看到这条消息的,怎么又想起当年那个小婴儿的?
每当想起这件事,我都有一种不由自主想冲上街跑两圈的冲动。似乎事隔了很多年以后,老战友们又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做了一件事。
就像崔健唱的一句歌词:嘿,老子根本没变!
这期间我有一次去成都出差,特意选择住在新希望集团总部旁边,跑过去站在楼下仰望了一会儿“新希望集团”的大牌子,但没有硬去联系人家。
张总更是一家子好人,但他们父子俩这次对采访基本都婉拒了。我也能理解,而且太理解了。
如今这年头,有些事无须说得太清楚。我就当我们心照不宣,只是偶尔给他的朋友圈点个赞,还不敢点得太频繁。
我在微信里问了下刘丰:你妹妹怎么样?出去打工了吗?
他说:心脏还行,这几个月都没用过起搏器;但她免疫力不好,经常感冒,一次总得打几天吊瓶。我们就哪也没让她去,在家养身体。我妈前几天骑电动车腿摔成了粉碎性骨折,我这边经常有债主……反正,还是挺难的,精神压力很重。
他在南方跑运输,整天帮人把汽车从这里运到那里,一看也是整天疲于奔命的样子。
如果刘帅再有下一次怎么办?还指望社会帮助吗?
再一再二,不能再三了吧?
可是这样的机率很大。万一……又该怎么办?
去年刘帅出院以后,刘丰给我发来两张照片。原来三月三号是刘帅的生日,吃蛋糕的时候他给拍了两张,发过来说:感谢冯叔,没有你我妹妹过不上这个生日。
我回了两条语音,大意是让他平时跟刘帅多教育一下,会说点话,办点事。社会帮助了你们,不图你们回报,但需要你们会表态。这样将来的日子才能过得更好。不然的话压力会很大。
他马上回我:冯叔你说的有道理,我明白你是为了我们好。我平时多教育教育她。
其实我心里还是没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