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人间|野草原上的范雨素:命若菜籽,落处生根
《在人间|野草原上的范雨素:命若菜籽,落处生根》
范雨素,如同野草原上顽强的生命。她的命运像菜籽一般,漂泊而渺小,却有着惊人的生命力。出身平凡甚至贫苦的她,历经生活的磨难与波折。然而,她并未被困境打倒,而是在命运的每一处落点生根发芽。她用文字讲述自己的故事,那些故事里有底层生活的艰辛,有对梦想的执着。她像野草原上不被关注却默默生长的草籽,在岁月的缝隙中,在生活的泥沼里,书写着自己的传奇,以坚韧的姿态在人间展现出生命不屈的力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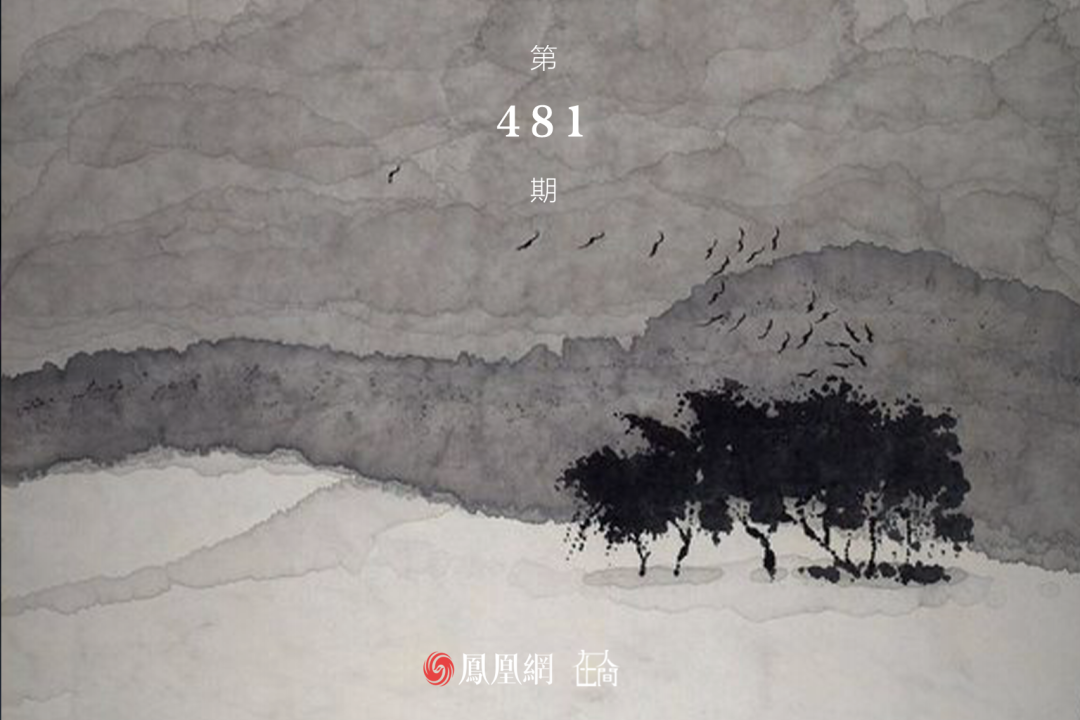
撰文|范雨素
编者按: 今年是武昌建城1800年,抖音中秋登楼夜晚会将于八月十五中秋节(9月29日)在抖音正式播出。六神磊磊、都靓、《长安三万里》剧组、以及抖音上著名的文化学者等也将悉数亮相,与天下爱诗之人以诗会友,共庆佳节。从八月初一直至月满中秋时,抖音还将邀请十五位作者分享唐诗与他们自己的故事。其中之一,便是范雨素。
范雨素是湖北襄阳人,和唐朝诗人孟浩然是同镇乡邻。她从小与唐诗结缘,在北京生活20多年,做过育儿嫂、小时工,6年前因为一篇《我是范雨素》受到关注。今年,她出版了新书《久别重逢》,并尝试成为一名专职写作者。最近,范雨素参加了抖音短视频版《唐诗三百首》项目,三百多万网友听她讲述黄鹤楼下楚人们的流散往事。

我没有去过黄鹤楼。
记得幼时,堂屋里的中堂画是松鹤图,堂屋里供奉的是仙鹤。小学五年级,课本里有一首古诗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,前两句是“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”。那时觉得好亲切,孟浩然住过的鹿门山就在我们镇,站在家门口能看到那座山。我的两个哥哥在山下上过学,亲姐曾在这里教过几年书。
襄阳孟夫子,“风流天下闻”。小学二年级读孟浩然的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”,只觉得是隔壁邻居家老爷爷写的诗。写《枫桥夜泊》的张继也是襄阳人,距离我们村远一些,有几十里路。
或许是受这些影响,我们那里的人特别重视教育。听我大哥说,当时一个同龄人读到初一,不想读书了。他的父亲靠贩米赚钱,挨家挨户收大米,绑到自行车上,到城里叫卖,赚取差价。听到自己的孩子不再上学,他立刻没气力骑车了,因为赚钱没动力了。
1985年,我上初一,好多同学在鹿门山玩的时候,看到一些日本人来寻访孟浩然的古迹。那时候鹿门山就是一座秃山,特别穷,没有景点,镇上也没有一个像样的饭店,后来就没啥人去了。张继写的寒山寺成了热门景点,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“网红打卡地”。
我的大哥比我大10岁,喜欢诗词,热爱文学。八十年代文学热,到处都是文学青年,很多人觉得好像写篇文章就能改变命运似的,我大哥也是这样。他买了好多好多书,很多人不理解,问我妈。我妈说,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,他这个年纪喜欢看书就看吧。
后来,楚人们陆陆续续离开家乡,去了大江南北,黄河两岸,经商打工。九十年代初,我在小学当民办教师。学校的一个女老师经常接到邮局寄来的汇款单。在广东打工的两个弟弟每个月把钱寄给她,再由她转交给父母。他们那个工作,每次能给家里寄好几百,我羡慕极了。我舅舅家有三个孩子在福州打工,二伯家大姐的老大从兰州大学毕业后,在湛江找了一份公务员的工作。
我大哥高中毕业复读了一年,还是没考上大学,或许是精神压力太大,还是回家种地,给人修过自行车,卖过手扶拖拉机。后来大家都出去打工,拖拉机卖不出去了。他离开家乡,到重庆修地铁,干了十几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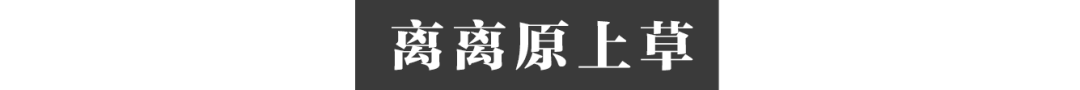
1994年,我也来了北京。因为性别的原因,基本上是家里人把你像水一样泼出去了。九十年代末,我住在东三环的十里河,三环还是城中村。经常经过的马路上,有一个小饭馆,起的名字叫“原上草”。我没有去里面吃过饭,但每次骑着小三轮车经过那里,都会觉得特别亲切,想起《敕勒歌》里说的“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”,想起白居易的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。
早在我四岁的时候,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就教我背过这首唐诗。那时我们小孩子睡在一张床上,她没事就在被窝里教我,“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”。
当时我经常在天桥上摆摊卖旧书。那时候年轻,没有恐惧,没有焦虑,不仅每天都干,而且特别有信心。大家觉得一定能挣到钱,想着能在北京买间房,两眼放光。当时这个目标并不难,工地上的广告牌,晚报上的房屋广告,几万块一间。摆摊的时候,每天都会遇到很厉害的人,没有人会说你什么,大家态度都非常好,不会去区分谁是底层,谁是高层。
路边的工地上挂着红布,写着“首都图书馆”。我当时天天想着快点盖好,这样就可以经常去看书了。后来图书馆终于建好了,我也搬走了。后来我的日子过得不如意,一个人带孩子,成了单亲妈妈,一年要搬两三次家,就想起“离离原上草”,想起“万里悲秋常作客”,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
宋僧有偈诗:“俱胝一指头,吃饭饱方休。腰缠十万贯,骑鹤下扬州。”和尚说,如果人一直保持着人之初的本来面目,饿则食,困则睡,就可参禅。但少年的人都有数不清的理想等着完成。要腰缠十万贯,要挣大钱,要衣锦还乡。要骑鹤下扬州,名扬海外,得道成仙。
现在我50岁了,到了“知天命”的年纪。人的命运跟植物的生长规律大概是一样的。古人说,人生一世,草生一秋。二十几岁的盛年,会把一切想象得很美好。当你想到自己是菜籽命的时候,已经是中年了。就像陶渊明写的,“盛年不再来,一日难再晨”。
我觉得“离离原上草”写的就是我。以前我说“人生是颗菜籽命,落到哪儿是哪儿,落到肥处是颗菜,落到瘦处是根苔”,野草和菜籽是一个意思。
现在整个中国变了,大家离开了土地,都是流动的状态。每个人都成为一个飘萍,不就是跟野草一样吗?按照物理的说法就是,每个人都“粒子化”了,能确定的只有自己。
我希望自己有野草那样的生命力,总也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
